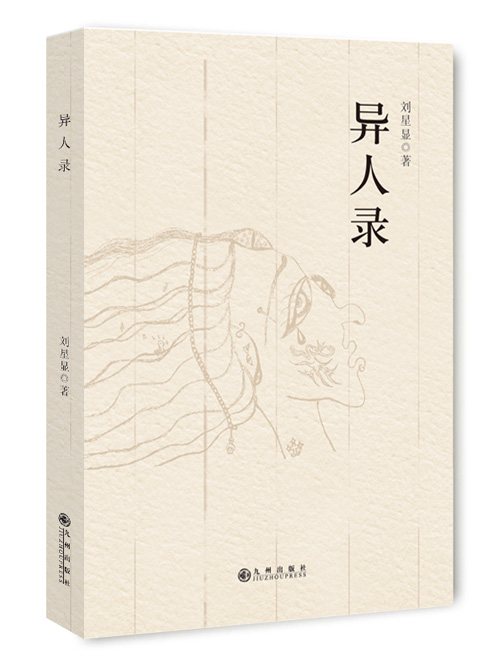
在斑斓的世界中,形形色色的人们皆有秘而不宣的微妙心理,每篇小说均选以契合主题的颜色,与读者进行一场智力游戏,试图掀起隐晦的人性一角,揭示人性中也许并不明媚的画面。这些都市异人们都在社会现实与自身欲望之间苦苦挣扎,或压抑,或放纵,或堕落,或孤独,或欺骗,或妥协,回应着这个矛盾的时代。
刘星显 男,生于1982年6月,汉族,吉林长春人,吉林大学法学博士,现就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。
主要从事法律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,一方面从事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,同时坚持文学创作,曾出版文学作品两部。
蓝·阿豆
褐·魔术
紫·如厕
赤·火机
黄·葵花
黑·献祭
橙·回旋
粉·簪子
白·蛾子
檀·轮回
青·卡牌
灰·凸鼓
绿·卤蛋
棕·腐肉
绯·一膳
跋·自解
蓝·阿豆
“最后一次见文阑是什么时间?”
“九月八号。一起吃烤肉。”
“只两个人?”
“是。”
“他当天精神如何?我是说……”
男警把手伸到空气里抓了抓,抓到一个令他满意的词。
“神志。他神志正常不?有没有反常举动?或者,说了什么奇怪的话?”
八号晚餐的情景历历在目,用不着费力回忆。不过,为了显示认真配合的态度,欧阳还是佯装翻翻眼皮,顿了顿。
“作家嘛。跟普通人比是不大正常。要不,就不能叫‘作家’了吧?”
欧阳故意摆了副滑稽又无奈的姿态,引来面前的女警会心微笑。
一男一女。看得出关系暧昧,眉宇间的青涩展露无遗。
在整个漫长的青少年时期,他们肯定遭受无数课文的摧残,被迫死记标准答案,笼罩在一群弄墨文人的阴影之下。如今脱身而出,恰巧逮到个作家,那感觉肯定与捕获个扒手不同。
看起来,他们对文阑的精神问题很感兴趣。只是欧阳还没搞清楚,究竟有问题还是没有对文阑更有利。
“你看没看过这个?文阑最新写的文章。”
女警从文件夹中抽出一沓稿纸递到欧阳眼前。欧阳接过,一面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取出眼镜盒,一面调整距离,眯起眼睛。
题目叫“阿豆”。
“哦……没看过。”
纸上的字清秀飘逸,仿佛无骨,多数溢出格子。字与字缠绕在一起,撕扯不开。文章没有分段,字间距很小,似乎笔头已跟不住思维,索性信马由缰肆意狂奔。
“你觉得这文章写得怎么样?”
“文阑先生的小说贯以严肃的国民性批判见长,大有鲁迅遗风,语言艰涩,擅用隐喻,意象丰富。比较起来,这篇选取家庭题材十分罕见,行文风格大相径庭……”
一时间,欧阳忘记了听众,自顾自讲演起来。说了半晌,才发觉场合不对,抬头一看,两位如坐针毡。男警似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,周身发了痒。一直在做笔录的女警此时在低头扣指甲。
“不好意思,职业病犯了。”
三个人同时一笑。两警察对视了一下。
“欧阳先生,我们不关心文学上的评价,而是想通过这篇文阑最新写的文章,结合你对他的了解,帮助我们来判断一下……”男警察又抓了抓空气,“他是否‘正常’。不是身为作家的那种正常或不正常,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或不正常。”
“你是说……”
欧阳摘下眼镜,扬了扬手中的稿纸。
“没错。我们怀疑文阑……”
没有继续往下说,也许是为了保密。两名警察脸上同时显出严肃的神情,这让欧阳觉到责任重大,似乎文阑命悬一线。
“能不能让我回去认真看看,然后再谈?”
欧阳使了一招缓兵之计。话刚说完,却捕捉到男警嘴角泛起的一丝略带嘲讽的笑意。
既然没有认真读过,刚才却侃侃而谈、唾液四溅,多少有些滑稽。只是,这乃评论界中再正常不过之事。欧阳早就练成了扫一眼内容简介,随意翻翻,便可迅速码出一篇有模有样书评的本领。或者说,这其实是做这行的必备素质之一。每一种行业都有“核心机密”,这些东西既不能明言,又不应被人发现。
实际上,欧阳也察觉了警方那边的“机密”,就是他们倾向于认定文阑存在精神问题,言谈间,警察已多次暗示欧阳需提供这方面的证词。
“原件不能给。”
男警显出不耐烦的神情,眉头紧锁,忽然攒了口气,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妥协,“这里有复印件,从文章里截出来的,你可以拿回去瞧瞧。”女警收回了原稿,又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递到欧阳手里。
草草一瞥,复印件上划了不少标示重点的横线。意思再明确不过了,看来他们已做好了“断章取义”的准备。
“那个……最近在文阑身上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吗?他最近受没受什么刺激?”
男警把身子探过来,盯着欧阳的眼睛。看来,他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。
望着墙壁上挂着的石英钟,时针已快指向七点。腹中空空如也,办公室散发出来的腐朽味道愈加浓重了,欧阳想尽快逃离这一块是非之地的愿望越发强烈。
“今年文阑为离婚的事情忙了一段时间。如果说‘刺激’的话……”
欧阳本想说的是以下的话:“如果说‘刺激’的话,也谈不上。文阑根本没把离婚这事放在心上,只是这个过程会耽误一些时间。要说近期发生了什么特别事,只能数这个了。”
但仅仅是停顿了一下的工夫,完全没等欧阳反应过来,男警便抢了白:“离婚这事对文阑是一个极大刺激。我们这里有不少案件。”男警随意拍了拍手边的卷宗,“婚姻出问题,很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。不用说那些农村的案子了,去年,工学院的许教授就用斧子砍了妻子的脖子。砍完了,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,然后去上课。你应该晓得。”
欧阳自然记得那桩轰动一时的案件。他坐在把屁股咯得生疼的椅子上,终于捋顺出眼前这位警察的思路:离婚引发刺激,刺激导致失常,理性的工学教授尚且如此,身为作家的文阑因此发了疯,做了荒唐之事,更在情理之中;尤其,还有眼下这篇文章作为证据。
欧阳打心底里对男警的推论不以为然,甚至想建议对方好好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左夫兄弟》,或者芥川龙之介的《竹林中》,好好琢磨一下一桩人为塑造的案子是如此偏离事实的。幸好,他及时打消了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,反过来,或许还不自觉地点了点头。
“那晚文阑没提离婚这事,但说起来文学史上有名的坏女人时很亢奋……”
八日的餐桌上,文阑确实畅谈了一番文学中的坏女人形象,引子是欧阳想在杂志上策划一期这方面的专题。《奥赛德》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,《驯悍记》的凯瑟丽娜,《痴人之爱》的娜奥密,等等。言及专业时,文阑惯用书面语,若直接把那晚的话印成铅字,恐怕便是篇不错的论文。尤其乘了酒兴来谈,形容为“亢奋”,一点也不过分。
明知警察会曲解为“牢骚”或“愤恨”,但欧阳依旧陈述了这条事实。他不得不又吸了口一直绕在面前不肯消散的烟气,方察觉自己在此时此地所扮演的应是相声表演中的捧哏,并且不得不进入角色。
“这与我们掌握的一致。”
男警边说边起身踱到饮水机前,接了杯水,递到欧阳面前,“这段婚姻早就出了问题。文阑在长期的抑郁下出现了一些幻觉,离婚的刺激最终让他精神崩溃。结果是,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妄想,把一条狗当成自己的情人,并且伴随着严重的幻视、幻听,出现了‘畸恋’。所以,在那条狗被小孩儿踢时,文阑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对孩子进行殴打。当孩子家人把狗打死时,文阑目睹了整个过程,心里瞬间崩溃,做出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。一切合情合理,只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。”
欧阳没好意思把纸杯里的水一下子喝干。液体滑过,润泽了干燥的喉咙,他咂了咂嘴,品出一丝甘甜。不知怎的,那一瞬,欧阳心里忽然涌起对眼前这位警察的感激之情。不可能只是为了一杯水的缘故,也许是为他们终于在文阑的问题上合作愉快而倍感欢欣。
接下来的谈话十分顺利,若非久未进食而略感体力不支,欧阳应该还会主动谈一谈文阑在大学时代跟他初识时的许多掌故,恐怕大多可被解读成为今朝之事的萌芽,想必也会让那位女警睁大了眼睛——她要是不总皱眉,看起来还真有几分姿色。
不过,一阵不由控制的胃鸣打断了合作的节奏,欧阳抱歉地笑了笑。谈话这才终止,男警扬头看了看钟,狠狠伸了个懒腰,问对面的女警:“假中介那个案子录几个了?”女警翻了翻:“录了三个,一千二吧。”
“怎么这么少?”男警的手指敲了敲桌面,“外面还有几个?”
“好像还有五个。”
“够拘了。得让他们回去再找找被骗的,搞个‘大额’不成问题。”
二人低语一番。从男警的神情来看,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。女警暧昧地笑了笑。欧阳在旁静观,揉着太阳穴,倒怀念起给他做了三年秘书的陈小姐来了——若她还留在身边的话,估计自己的事业还会精进。一想到手头还有一篇推新作家的书评要写,头就疼了起来。
“来签个字,按个手印吧。”
“签这里。”女警递过来笔,印泥也准备好了。
女警的字很难看,像一只只死苍蝇,佝偻着身子,陈尸在格子线上。欧阳想掏出眼镜看看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,却被一声不耐烦的“签吧”阻止了动作。他猫下腰,在签名的当间使劲屈了屈眼睛,好让字清晰一些,看到的却是一大堆自己没说过的话。“离婚”、“发病”、“刺激”、“异常”、“崩溃”……单瞧字眼儿,很熟悉,连成一片,却很陌生。但,他丝毫没有挣扎,爽快地在签名上按了鲜红的指纹。直起腰时,感到一阵眩晕。
“还要签一份。”
男警从另一沓稿纸上面取来几页订好的翻到最后,摆在欧阳面前。字仍旧是苍蝇形的,仿佛能听到它们嗡嗡作响。刚要落笔,听见男警说:“签‘孙靓’。”
“什么?”欧阳停了,抬起头。
“在这里,签‘孙靓’。”男警指了指。
“孙靓?”欧阳重复了一遍这个陌生的名字,瞬间冒出来许多疑问。
“一个骗子,开了个假中介,介绍大学生家教的。”男警料到欧阳要问什么,轻描淡写地解释道,“要凑够钱数和人数……对了,不是‘明亮’的‘亮’,是一个‘青’加一个‘见’,‘再见’的‘见’。”说着,男警笑了笑:“我一直都念‘孙倩’。让你这搞文化的见笑了。”
最后一句有故意露怯的意思,听得出,是友好的表示。欧阳领了这份情,再没犹豫,换了一种笔体签了名,按上自己的手印。作为某种交易,欧阳立即提出见文阑一面的要求。
“后天下午来吧。那个时间可以让你见一见。”临出门前,握了握手,算是约定了,“麻烦叫下一个来这里。”








